这里,装着不少钱塘人的“执念”!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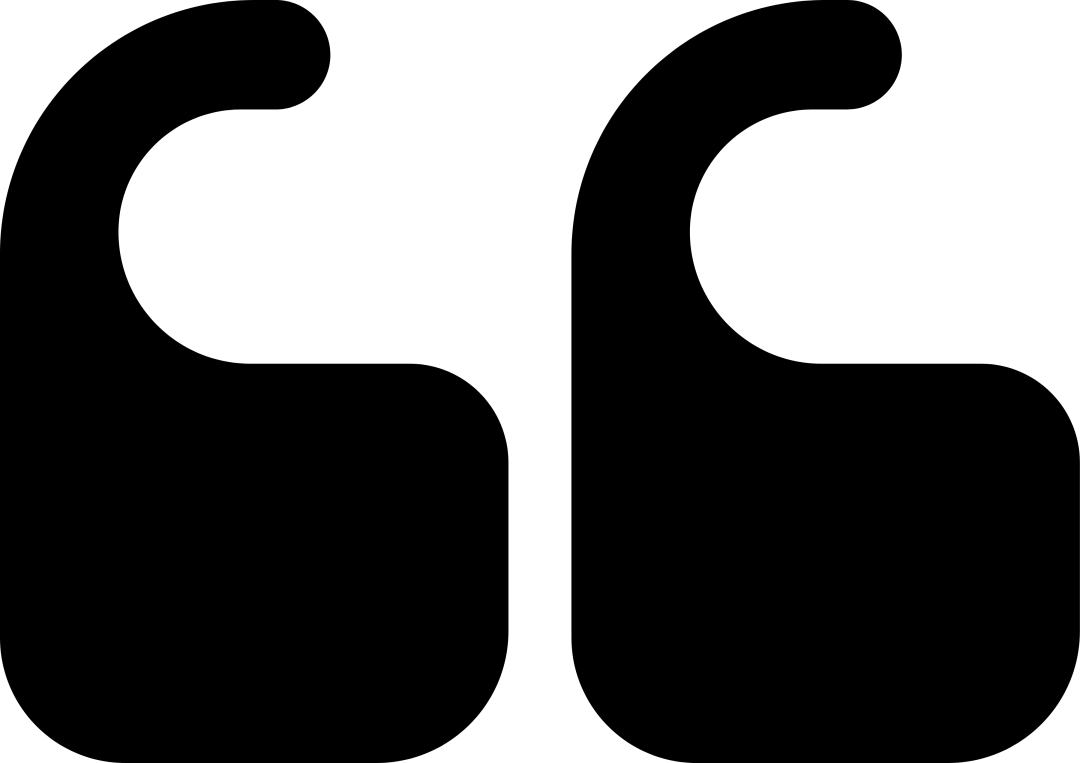
在我心里,总氤氲着一个菜园情结
有人说,城市是农村养大的
而我在想,那供给农村的养分又是什么?
答案是肯定的:
是广袤的田野和青青的菜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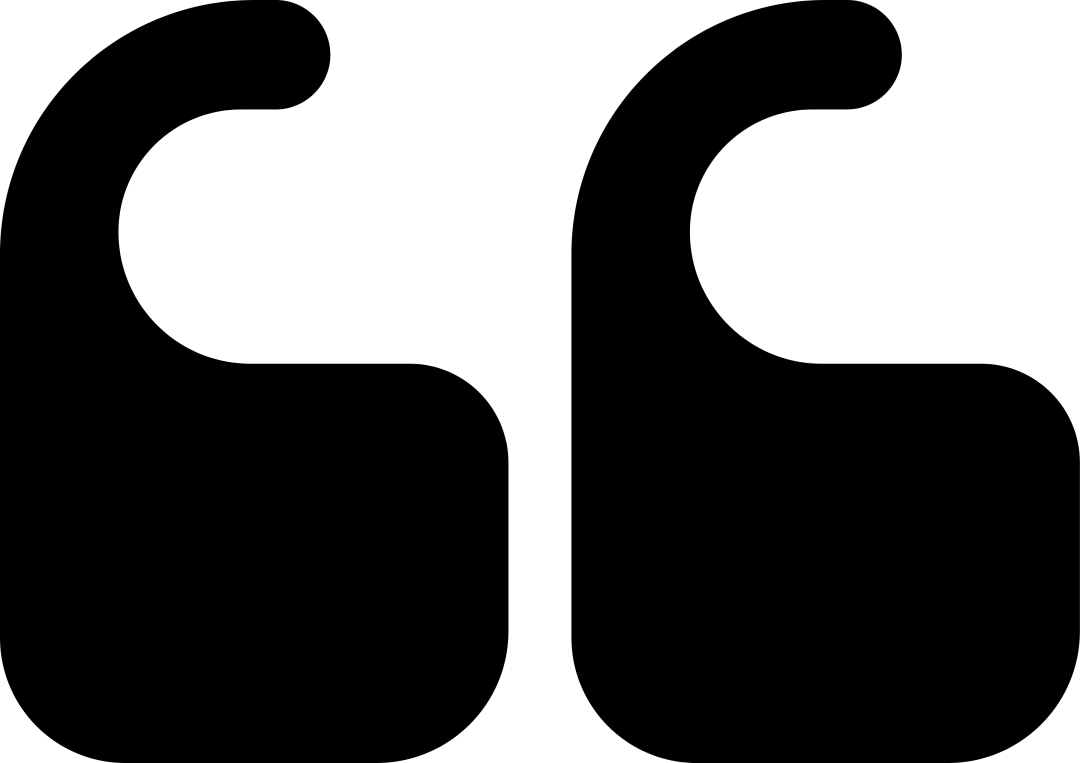

我热爱菜园,不仅仅是因为菜园哺育了村落,还因为它曾经作为一个容器,盛装着我童年和少年一段青涩的时光。
我的故乡在江南。江南多山,但只要有泥土,无论哪一块地,拿起锄头挖上半日,就可以成为四季葱郁的菜园。你看,屋前屋后、山脚溪畔,它们就像天堂遗落的彩珠,散落在村庄四周,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,装点着山村的安谧、寥落与纯朴。

陶渊明向往着“种豆南山下”的生活,我却总是为菜园那生生不息的杂草懊恼不已。七月,天空是明晃晃的,土疙瘩是明晃晃的,甚至所有的菜叶都反射着耀眼的白光。我隐匿在菜畦之间,耳畔热气呼呼直响。草是“疯子”,在蔬菜地里遍插旌旗,明目张胆地“喧宾夺主”。我的任务是在它们成气候之前将其剪除,并将它们“暴尸”于烈日之下。
这原是一块荒滩。如今,这儿篱笆、土墙阡陌纵横,被分隔得如棋盘、如迷宫。我置身其中的一个角落,野草如森林一般遮掩着我的身躯。随着它们一根根被连根拔起,形成垛子,荒芜的菜地渐渐清朗起来:辣椒树亭亭玉立,稀疏的绿叶间,挂着几个干瘪的辣椒,使人不由地想起沙漠上寂寞的驼铃;茄子树形容枯瘦,土褐色的枝干如老母鸡那只剩一层皮的爪子,若不是隐藏其中的几朵淡紫色小花,真看不出它还有一丝活着的迹象……

这就是我的菜园?这就是一年四季供应我一家近十口人菜碗的全部后方?那时,全乡都没有菜市场,即使有,又有谁会去买菜呢?家里的谷仓,一到青黄不接时都还敞着个空肚子呢。我的心在隐隐地痛。
汗、泥沾满我黑瘦的小身躯,赤裸的脊背被晒得发亮。荒草丛里,教室里的清凉和书本的芬芳,显得是那么的缥缈和遥远。怎么还不开学呢?而此时,我只能低着头和那杂草进行一场“生死存亡”的较量。四周静悄悄的,没有人语,没有虫唱,如一座被人遗弃的孤岛。
当太阳西沉,炊烟四起之时,菜园终于热闹起来。从生产队归来的人们,一个个肩挑手提尿桶、土箕、锄头,纷纷来到自家的地里忙活:种菜、浇水、整地、搭瓜架,调侃之声如稻浪起伏。不久,远方传来妇人唤归的长调,一天的辛劳就这样拉下了帷幕。

几场阵雨过后,菜园又开始充满了勃勃生机,变得绚丽而丰富。丝瓜藤爬满架子,葱葱茏茏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,一朵朵黄花在绿叶中调皮地探出头来,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;空心菜水灵灵的,紫色的花朵喇叭样面向蓝天,隐隐约约有热烈的音乐在奏响;南瓜一个个从架上垂下来,黄澄澄的,似某个艺术走廊上悬挂着的一排排喜庆的灯笼;柿子红、茄子紫,豆荚一挂挂;蜂舞、蝶飞、虫唱,还有弥漫于空气中各种菜蔬的清香——整个菜园葱茏馥郁的有如一个热闹辉煌的洞房。
而我从无心思欣赏。欣赏只是那些离开了乡村的城里人的一剂心灵药。我注意的是,黄瓜什么时候挂果,西红柿什么时候成熟。在锄地、捉虫的间隙,我会突然停歇下来,把它们摘下来捧在手里,用沾满泥的手随便一擦,就往嘴里送。那时的感觉,比猪八戒吃仙桃都还有滋味。
菜园是无私的。她总使我想到伟大、慈祥、奉献等关乎崇高的字眼。她如河流、稻田一样,哺育了村庄、哺育了社会、哺育了历史。在某一个季节里,我跟着父亲在菜地里有模有样地松土、起垄、开沟,然后猫着腰一行行地点菜籽或散菜秧。间隙,父亲会传授我种菜经:什么菜应深种、什么菜应浅种,什么菜喜阳、什么菜喜阴,什么菜宜密、什么菜宜疏。而我却总是关心着地里忙忙碌碌的蚂蚁和被锄断为几截的蚯蚓,还有那五彩的瓢虫、笨笨的蜗牛,间或追赶着彩蝶和蜜蜂……

每天早晨,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哥哥抬水桶浇水。一桶水,一半是浇在了菜苗上,一半是浇在自己身上。我总是在浇水时,把水瓢往空中一泼,然后半遮着头喊:“下雨喽,下雨喽”。一星期后,菜苗拱出了地面,扎稳了根,浇水才告一段落。看着那绿油油的一片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,天天往菜园里逛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了。
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,万物生光辉。”不知不觉我长大了,才恍然发觉,青青菜园已不知什么时候成了我生活中的遥远。在低吟着“何时复西归”时,自己已泪流满面——想不到,一块不大的菜园,竟成了我生命中一份沉甸甸的眷恋。
*本文图片由AI生成
